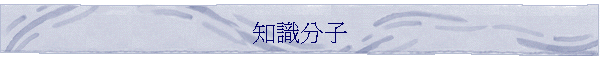
知識分子
他去醫院的時候父親正熟睡,被單蓋至頸項,剩下一具蒼白的面容。他從來沒有這麼仔細地看過父親的臉。父親的皺紋,像幾條平行的河川在額間;眼前的魚尾紋
是扇形的三角洲,眼窩處有兩圈深深的黑眶;唇色白裏帶紫;鼻間的氣息絲絲如縷。
父親病得很重了。他已經有兩週沒有來醫院這麼坐著守住父親。原本是與兄弟輪班的。但是輪他值夜的時候,父親疼痛唉唉哼哼,卻沒能吵醒他;父親要上廁所,喚他兩聲,他也沒聽見,父親只得自個兒攜點滴瓶去了。
父親對他兄弟說:「半夜別讓辭修來。他很累。」所以都是他的兄弟值班。
他週六週日常有演講、聚談及其他各類文化活動,也是匆匆見著父親,匆匆離去。其實他心底很清楚與父親相處時日所剩無多。時候不對的電話鈴響起一定與父親的死訊作聯想,驚得他半跳起來。他實在應當多與父親在一起的。
但是一天天過去,他還是忙個不停。他的生活型態,早與家人不同。父親只有小學畢業,一生作黑手;他的兄弟高中高職畢業,一個作直銷一個跑外務,沒什麼太光明的遠景,倒也安分守己,有妻有子女,守住一個家。只有他是美國比較文學博士回來的。學識,外加口才、機智與挺拔的外表,使他在文化界好出
鋒頭,什麼拉里拉雜的演講題目,掛上他的頭銜,就有一定數目的聽眾;專家學者的聚談,也以邀得他為好興頭。
他在外頭居住,父親兄弟都知道他很忙,素來容讓他,不要求什麼。這種容讓,早在他顯出讀書興趣的中學就開始了。家中瑣事也不輪他擔,家計不讓他操心;下課回來,直直走向書桌,喊他半晌才應。打從他坐上書桌,電視機就扭得小小聲,談話也壓低了嗓門,全家人都順著他讀書第一。連母親過世,喪事之對內對外,都只由兄弟出面。親戚看不過去,說他,父親就護著說:「隨便他去!我們張家真難得出一個讀書人啦!」邊說,邊看著自己那雙粗糙的手。
母親過世前他也是不常去醫院。那時他讀大學,專心於期末考,每天黃昏,到操場上跑五千,邊跑邊想,不知母親現在怎樣?想到用情處,就讓思想跳開了,覺得課業好沈重,期末考非得考好不可。
去醫院看母親,母親握住他的手像握住指望:「全厝的人都依靠你,你一定要出頭天。你爸爸兄弟都不是讀書人。」他的心很沉重,滿肩重擔。跑五千時便直直加速,想讓重擔遠遠跌落在身後。
母親過世了。他更加走進他的知識領域,又遙遠又疏離又清高。其實他心裏也清楚他是可以推掉些演講、聚談的。只是去醫院的心理壓力很大,相較下那些演講聚談,就魅力足夠、難以推卻了。
他有懼怕。當他走進病房,看見父親熟睡著,毋寧說是大鬆了一口氣。父親最近已很難得熟睡了。癌症末期的痛楚常叫忍耐力強的父親唉哼出聲,那一定是痛到常人
難以忍受的程度。最近他常叫著,難得熟睡。他踱到窗口,眺望戶外。一個小小的天井下是一片小小的草皮。這是一間收費昂貴的小私立醫院。醫生說父親不行了,兄弟就將他轉到這裏,讓他能圖個清靜,少受些人聲雜沓的叨擾。
他很驚異他兄弟處理父親的臨終,是如此的明快果斷出錢出力,他的嫂子與弟媳也捲進這場服侍裏,理所當然毫無怨尤。他們很少起爭議或討論,就是一個意見、一個動作,像一群無聲而方向
一致的工蟻,將自己完全擺上,來與父親一同承擔痛與死。這種愛的力量究竟從那兒來的?為什麼他沒有呢?
他聽見父親呻吟的聲音。父親終於醒過來,要面臨另一場痛苦的爭鬥了。他坐在父親床邊的椅子上。「是你啊!怎麼有空呢?」父親的聲音很微弱。
「今天沒事!今大沒事!」他喃喃答,心虛而自責的。父親在床上輾轉著。如何分散他的注意力,讓他不痛楚呢?「最近接了些演講,都是很有趣的,像是『如何談戀愛』啦!『婚姻與性』
啦!『如何過有意 義的人生』啦!『人際關係與溝通的藝術』啦!」
「哦!」
「也幫忙弄了些戲劇。怡君是學舞台設計的,有夥搞小劇場的朋友。」
「哦!」
「結果不正經事業,倒比教書這事業更忙了。」
「哦!」父親假裝有興味,卻仍是輾轉,不小心呻吟了一下。
他覺得燥熱,忽然站起身來,又坐下。父親對他總是沈默著,好像以為自己沒有什麼分量跟知識分子對話。可是父親的沈默使他覺得自己很可笑。特別是父親與他的兄弟可以談上個把小時,無非是家居的小事,親友的芝麻綠豆,談得鄭重其事,而他竟插不上口,只覺得瑣碎、煩悶、無聊。在他們之間有一道非知識不能跨越的溝。
他以為父親與兄弟乃普羅大眾之典型,關懷的層面僅及家族,天下的事,只要不殃及自己,是無動於衷的。所以他這個關懷層面已遠遠逾越小我及於大我的知識分子,與他們隔閡之深,只能叫
父親對他的生活、話題沈默以待。
他剛回國時,曾經對兄弟有些不由自主的輕視;對自己的學識、社會地位有些自負;當親戚以敬重的態度向他寒暄時,有些陶陶然。這就是他的懼怕。因為父親瀕臨死亡時,他徹底看出自己只能以清談關懷遙不可及的群體,卻對至親沒有付諸行動的力量。
父親又在呻吟、痛苦叫他的臉扭曲掙檸。
「我能為你做什麼?」他大聲問,又站了起來,再坐下。
「去問,快快去問護士止痛針什麼時間才能打?」
他快步走出去,又沮喪的回來。
「還要兩個小時。不能太密的。」
父親絕望的大聲呻吟起來。他恐懼了。他多希望他兄弟就在身邊。他們總是知道該怎麼辦的。
「我能為你做什麼?」他又問。父親沈默。但呻吟。
啊!話題,話題,讓我再想個話題。昨天他才談了一天的話,從街頭抗爭、群眾心理,談到消費者心態、廣告企劃,談到環保以及
知識分子的良知。
「辭理說他一下班就過來。大嫂煮了雞湯麵線一道送來。」
「哦!」
「大嫂……真不錯。沒想到相親可相到這麼好的。」
「是啊!」父親大聲叫了起來。
他慌張的跑出去找護士。護士見他白了臉,趕忙衝進來。父親已按捺下叫聲,忍耐著,扭曲著臉。
「我幫他打止痛針!你跟我來。」走到長廊,護士悄聲說:「只是心理作用,打了也沒用,癌症末期沒法止痛的。痛到極點,累了就睡了。」護士給父親打了針,父親較平靜些。
「需不需要我為你做什麼?」他又問。
「……你……也該結婚了。」
他低頭看自己的鞋。他與怡君同居父親是知道的。兄弟都說,換了是他們,這麼做一定會被父親打斷腿。父親對他卻保持沈默。其實遠從他考上大學,父親送他一隻手錶開始,就不大管他了。父親總是說:「他書讀得多,他知道的。」
怡君不要結婚。「婚姻對女人是個束縛。」她說:「我學的是藝術。藝術講究自由。」「No
marriage, No children, No kitchen.
」她說。怡君當真擺脫掉一切可能有的束縛,包括他的父親。父親生病期間,她沒來探望過一次。他對怡君說:「父親到末期了,好痛哪!」怡君看起來好認真的說:「好可憐!」也就只說了這麼句話。
「還是結婚沈穩些。最近這些時間,幸好是有玉美和小麗。」
他一直低著頭,沒敢抬起來直視父親的臉。父親又開始呻吟。距打止痛針只過了十分鐘,在床上輾轉著,比方才還難忍。怎麼辦呢?怎麼辦呢?哥哥的出現,簡直像救星一般,讓他鬆了口氣。「爸爸很痛。」他求救地說。
「麵線來了!麵線來了!」哥哥好精神的說:「玉美幫你丟丁好多香菇,是你最喜歡吃的小香菇,趕快吃,吃完擦個澡,比較好睡。你看,全新的三槍牌。」父親還在呻吟,卻也無力的笑笑。他從父親的笑容中看出一種完全的託付與信賴。
哥哥將父親的床搖起來,麵線一口口放湯匙裏,吹涼了,餵進父親口裏。父親吃得很慢,溫順而聽話的,像個病中的孩子。才吃幾口,咳一聲,全又吐了出來,吐得一身一床一地。
「沒關係!沒關係!」哥哥說,拿布慢慢擦父親的身子,再蹲下來擦地。然後又慢慢的餵。父親卻吃不下了。
「我們來擦個澡吧!」哥哥說。他木愣的站旁邊,看得心好苦,滿肩滿心的重擔壓得他透不過氣來,他覺得自己也要吐了。深吸一口氣,他匆匆看錶:「我,我,我……,」他對哥哥說:「我還有事。」
「去去去,」哥哥說:「這裏有我。」走前,他看見自己來時買的那束玫瑰,久置檯上,已萎縮了。一生從事黑手的父親,是不賞花的。哥哥幫父親擦澡時,他離開了。他想起那一次哥哥交代他為父親擦澡、他是如此的絆手絆腳,把父親弄得很不舒服。他從來沒
有這麼近的與父親肌膚接觸。父親蒼白瘦弱的身體他既不敢直視,也不敢觸碰,那樣親密的距離, 叫他害怕得好想逃避。他張皇失措。
他終於承認他沒有辦法承擔父親的痛與死。在愛的理念上,他是如此侃侃能談;在愛的實踐上, 他卻是個無法擺代價的侏儒。
那晚他赴一個演講「愛、生活與學習」。當他離開醫院,真實地感覺自己蓄意將滿肩重擔隨自動大門關上而丟棄,他從來沒有這麼痛恨過他自己的口才、機智與清談。